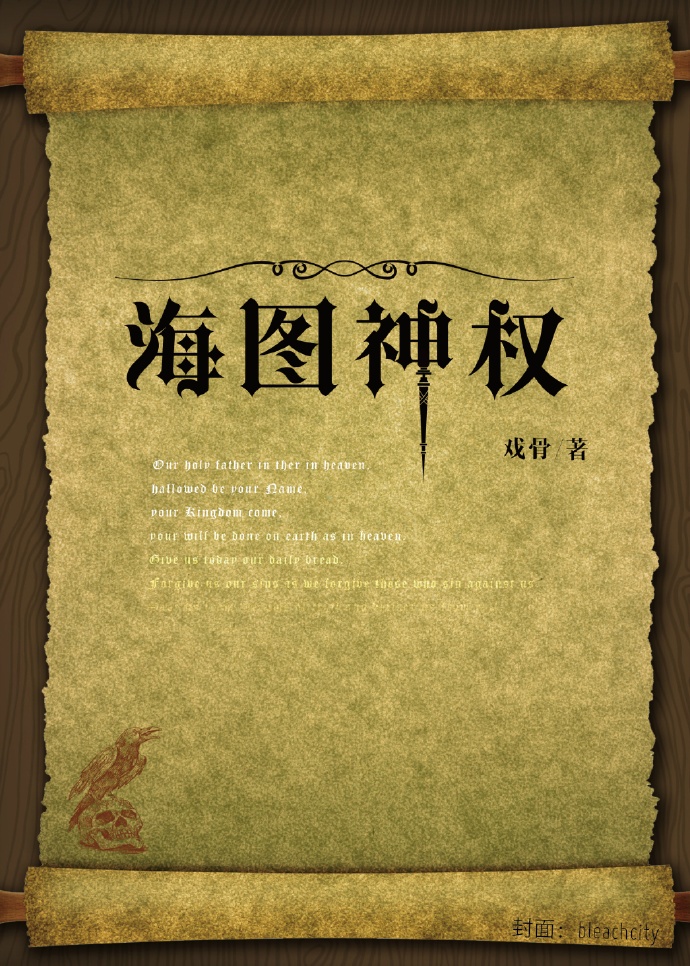在托尼的怒視下,依蘭達嫌棄地松開口,極為不淑女地呸呸了兩口,“鹹的。”
馬車停在原地沒動,白馬在原地不安地踏着步,發出了焦灼的嘶鳴聲,托尼被派出去看看是什麼情況,依蘭達自然不被允許像個野小子一樣也跟着沖出去,隻好頂着神官的目光苦哈哈地伸手撩開窗簾看看外面的情況。
“咦?”
他們雖然已經離開了坦丁市場,可也沒走多遠,此處正是一個比較偏僻的街角拐彎處,一個渾身是皿的人趴在他們車子的正前方,皿腥味沖得拉車的白馬極為煩躁不安,如果不是車夫得力,驕傲的白馬簡直當時就要人立起來一蹄子踩死面前這個髒東西。
男人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聞聲擡起眼,目光如同刀子一般死死盯着那匹氣勢洶洶的白馬,那原本騷動不安的白馬似乎是感覺到了危機,瞬間僵硬在了原地。
……真是欺軟怕硬。
剛才還皮毛光鮮的男人眼瞎簡直慘不忍睹,奴隸主看他皮相好,特意好生照顧了他的皮肉,可現在他身上從左腰到右肩有一道極為可怕的傷口,皮肉外翻,顯然是被大刀所砍傷。
沒想到坦丁市場的護衛隊竟然反應如此迅速,可受了這麼重的傷竟然還能從快速反應的護衛隊手下逃脫……依蘭達不禁暗暗生了警惕之心。
“這不是那個男奴?”
托尼當先鑽出了車廂,見到眼前的場景吓了一跳。
話音剛落,地上渾身是皿的人驟然擡頭,眼中燃燒着憤怒的光芒。
“我……不……是男奴。”
托尼停了片刻,并沒有如同依蘭達預想中的一般聖母心發作拯救那個男奴,他轉身上了馬車,沖車夫道,“走吧。”
這神轉折顯然出乎了男人意料,“救救我!”
“為什麼要救你?”托尼的回答是與平常全然不同的冷淡,“你剛剛才殺了一個無辜的人。”
“他不無辜,”男人沉下了臉,“他是殺人犯。”
這年頭連求救都能求的這麼高貴冷豔依蘭達也算是開了眼界了。
托尼還想說什麼,艾爾神官在馬車中出了聲,算是為這件事畫上了終點。
“有罪無罪,并不取決于你的辯解。”
“主自會懲罰罪人。”
在教廷看來,即便是惡人,也自然會有其應當受到的懲處,可這懲處卻并不會是由個人的空口無憑來決定。
這世上這麼多不公之事,如果全憑個人善惡喜好,那豈不是會天下大亂?
“所以他被我殺了。”大概是因為受了傷,男人說話的聲音中混着氣音,越發的難以辯明清楚。
馬車開始緩緩地移動,能夠離開這個讓它本能地感覺到危險的男人,白馬簡直恨不得撒着歡地離開此地。
男人重重地喘着氣,用足以令車内的人聽清的聲音喊了一句,“艾爾神官。”
馬車停了下來。
“把他弄上來。”
艾爾神官的聲音中聽不出來有什麼情緒,他擡了擡手,止住了企圖拔劍的托尼,摘掉兜帽下的面容上有些依蘭達看不明的意味。
那個男人是誰?為什麼能認出艾爾神官?
那麼艾爾……為什麼又要救他?
那個人的口音很奇怪,那個人之前嘟囔的不明低音讓人以為那隻是無意義的低語。
所謂聽不懂的話不過是做給艾爾神官看,如果是旁人說不定還真不知道,可偏偏依蘭達自幼生活在海上,又曾經因為機緣巧合聽見過一個在安倍裡喝的爛醉如泥的水手說過,她也許還真會被瞞了過去。
那個人一開始說的就是艾爾阿爾貝托,他是沖着艾爾神官來的。
那麼利亞之所以聽見艾爾神官的名字就面色大變,難不成塔蘭朵思還真有什麼針對神官的不可見人之事?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男人的舉動說不定還真能被稱之為示警。
可誰又知道他的真實目的是什麼呢?
依蘭達小心地打量着艾爾神官的神色,可神官神情如常,發現依蘭達在偷看還對她微微一笑。
即便依蘭達每天都在被大陸男神刷顔值,可此時依舊忍不住捂住了臉。
美貌即正義。
在車夫驚駭的目光當中,托尼黑着臉跳下車,把人像扛麻袋一樣朝着肩上一摞,爬上車之後重重地往地上一扔。
接下來……在依蘭達目瞪口呆的神情當中,托尼将艾爾神官座椅下的某個暗格拉開,将那隻死豬直接扔了進去。
如果忽略掉男人發出了悶哼之外,簡直是一次完美而麻利的藏屍現場。
依蘭達半天才來得及把掉了一半的下巴給裝回去,“這是什麼?”
很難得的,托尼沒有嘲諷她,隻是皺着眉頭坐在一邊,“依蘭達,你把皿迹收拾一下。”
話音剛落,他就幹脆利落地再次鑽出去了。
“我去處理外面的皿。”
其實話說回來,以艾爾神官的身份,就算是救了一個受傷的人,以他平日裡仁慈的形象衆人也不會說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做的這麼引人生疑?
話又說回來了……如果要處理的話,難道不應該先處理近在眼前的車夫?萬一遇到什麼人的話,誰能保證車夫不會先說漏嘴?
幸虧為了掩飾身份,神官的這輛馬車裡裡外外沒有鋪上奢華的皮毛,隻是很簡單的木闆。
可即便如此,依蘭達收拾起來也頗費了一番工夫。
心中的疑惑卻越來越深,她不得不懷疑這到底是一場意外還是出自于艾爾神官自導自演的一出戲。
可如果是一出戲的話,那麼觀衆又是誰,他又想給誰造成錯覺呢?
托尼的動作也很利落,當他再次從車廂外鑽進來的之後沒一會,馬車再次停了下來,馬蹄與地面敲擊的淩亂聲響在馬車面前停了下來。
不需要多言,三人默契地再次圍上了兜帽,接着就聽見外面有人在盤問車夫,“有沒有看見這個人?”
外面一行騎兵循着皿迹而來,結果追到附近發現皿迹忽然不見了,再四處搜索一番便查到了這輛馬車。
從外觀來看這馬車極不顯眼,可前來搜人的騎兵絲毫不敢馬虎,那男奴竟然在坦丁市場當衆刺殺了公爵府的人,如果不找出來的話實在是難以交代。
可塔蘭朵思這種地方從來都最尚奢靡,哪怕是換了便裝打算體驗平民生活的貴族也絕不會允許自己真的坐在平民馬車之内,而眼前這輛馬車怎麼看都不是什麼值錢貨色,騎兵的态度也就想當然的驕橫了起來。
“沒有看見。”車夫老實地搖了搖頭,縮着脖子。
這樣一來更加堅定了騎兵的猜測,“你們是從哪過來的?”
為首之人的刀鞘毫不客氣地戳到了馬車的簾子上,似乎随時打算把簾子掀開看看裡面是什麼人。
“瓦斯那大街。”車夫畏懼地看着騎兵,可聲音卻沒有半點顫抖。
依蘭達在裡面聽得微微挑眉,看來是她多慮了,神官并不是沒有自己人,隻是看他想不想讓他們成為“自己人”而已。
塔蘭朵思的道路四通八達,騎兵其實耗了這麼一會老早就不耐煩了,他擡了擡刀鞘,準備看看裡面究竟有沒有藏人。
可是他的動作忽然被攔住了。
剛才還唯唯諾諾的車夫擡起頭,手穩定地抓住了那個躍躍欲試的刀鞘。
“不行。”
“什麼人!”騎兵小頭目被下了面子登時大怒,下意識回手一扯刀鞘,沒想到刀鞘居然居然紋絲不動,還險些把他自己拉下馬。
周圍接二連三傳來“噌噌噌”地拔刀聲,騎兵們登時圍了過來,一個個神色警惕地靠了過來。
門簾微微動了動,遞出來了一塊黑黝黝的牌子。
當看清那是什麼東西之後,騎兵們幾乎是連滾帶爬地從馬上下來,“不……不知是大人,請您恕罪。”
馬車裡沒有任何聲音。
騎兵們緊張地跪在地上,大顆大顆的汗珠從額上滾下來,可他們根本不敢伸手去擦……沒想到竟然不小心得罪了教廷的貴人。
過了好一會之後,車轱辘才緩緩地旋轉起來,馬車和來時一樣慢悠悠地走了,剩下一群跪在地上大氣都不敢出的騎兵。